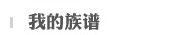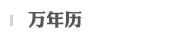好玩儿的刻瓷人:宁卖鞋不卖活儿
2011年12月15日
茅子芳的家,客厅改成卧室,只剩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六人同住一套两室一厅,显然有些逼仄。走进他的书房,八哥、金鱼、刻瓷、葫芦、玩具车、儿童贴画,各种互不相关的物品挤在一间屋子里。他说“我做刻瓷就是玩,石头、木头、葫芦,我都玩。”
他递过来的名片是用垫奶箱子的牛皮纸自制的,竖排版从右至左印着“工美老工匠茅子芳”,背面是印章字“糟老头子”。桌上一枚章,刻着前几天和徒弟从蔚县剪纸展回来遇到大雪的情形,他用刻章来记日记。
茅子芳首创的厚釉人物刻瓷,曾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此外,他参与设计制作的大型玉雕《韶山》,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做出的头一件。但他不希望别人叫他“大师”,他的作品几乎不参加任何评奖,不跟商人打交道,单位发不出工资时,宁卖鞋不卖活儿,人们都说他是圈内“怪人”。

刻瓷清末进北京
刻瓷的起源,说法很多,有说魏晋时就有,也有说源于宋明。我认为,艺术不能脱离社会,更不能超越当时的科技条件。魏晋时有瓷器,但胎、釉的硬度不够。宋代出现了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瓷器发展已完全成熟,书法、绘画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才具备了产生刻瓷艺术的条件。
北京的刻瓷业是清朝末年发展起来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府尹为了让八旗子弟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建立“农工学堂”,又叫“工艺学堂”。内设各种工艺科,其中“镌瓷科”由南方来京的华约三任教习。后来学堂改为“工艺局”,由原来的官商合办转为官办,“镌瓷科”改为“瓷工科”,有学生20多人。
体制变了,部分学生被商人带走,留下的人有的感到学习刻瓷艰苦,有的因生活困难,大都另谋生路。只有朱友麟、陈智光坚持下来。1957年,两人被聘为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过去的刻瓷师大多不会创作,别人画好底稿,他们刻,依然是给人当工具。
创作谜语混铅笔
我1943年生于北京,从小喜欢画画, 1956年初中毕业,一心想念美院附中,但家里太穷,就上了工艺美术学校,不用交学费,还管吃住。学雕塑专业是因为它最省钱,美术这行,花钱太多,要是读图案设计,颜料我就买不起。雕塑以素描为基础,买铅笔就行。那时候,我给《北京晚报》写谜语,写一堆投过去,登一条给一毛,能买根铅笔,够用一星期。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玉器厂。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朱友麟刻瓷艺术展”上第一次见识了刻瓷,看得我都走不动道了,开始用业余时间玩刻瓷,找个钢錾子,把家里吃饭的白瓷盘子、饭碗砸了不少。摸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刻出几件自认为满意的花鸟作品。
当时,从玉器厂到工艺美术研究所不过300米,我好几次想去向朱先生请教,又怕被人家拒之门外。终于决心厚着脸皮,用午休时间敲开朱先生工作室的大门。先生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不但没拒绝,反而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作品,从工具到技法都讲得非常仔细,最后嘱咐我好好学习刻瓷,把刻瓷艺术传下去。
按先生指导,又刻了几件,再去求教时,他已年迈多病。
1964年,朱先生去世,我这个“编外徒弟”只好靠自学了。
厌恶“小作坊”心理
初学刻瓷,听人家讲刀法分为“点、起、勾、跳、捻、转、擦”,听着都晕,简直不想学了,但真玩起来,也没那么玄。
那些“刀法”的出现,不排除在旧社会,一些手艺人为了保密故弄玄虚,尽力把自己从事的行业说得神乎其神,越难越好。
我讨厌这行当里的“小作坊”味,很多老师傅不爱露手艺,觉得“吃饱徒弟,饿死师父”。其实,越不让看的技术越是一学就会,没什么了不起,真正的“活儿”靠的是艺术而非技术。
刚到玉器厂时,有个老师傅,是厂里较少既懂设计又能制作的人。我们做一个香炉,要找这三条腿的位置,旧社会没人教这个,他闷头琢磨。我那时二十出头,爱气人玩,我说:您这点手艺,不过就是一张擦屁股纸。我拿起一张报纸,用折叠的方式给他演示如何迅速找三条腿的位置,然后把报纸一揉,说:这不就是擦屁股纸吗?他问:“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您要请我吃饭,我还能多告诉您点。他果真请我吃饭了,我告诉他,用量角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