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胜:《西游记》的成书与俗讲、说话
2013年01月23日
引 言
《西游记》的成书,学者一般将之溯源到《大唐西域记》,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对于玄奘和尚到天竺取经的本事的神化的考察,似乎还有较大的空间:小说中的说唱因素如何解释?小说与俗讲变文有何关系?西域的西游故事是如何传到中原的?宋代勾栏瓦舍中的西游故事来自何处?对小说又有何影响?等等。
另外,《西游记》虽然是关于唐僧西天取佛经的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曾指出的,小说的作者“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 [1]。《西游记》的作者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误以为是《多心经》。其实,“般若”是梵语音译,大智慧的意思“;波罗”为彼岸“;蜜多”为到达的意思。将《心经》误读为《多心经》,其缘由就在于一方面《西游记》的作者不熟悉佛典、不懂得佛典的教义;另一方面也在于小说的作者是将从西域开始流传、历经几百年在瓦舍勾栏里打磨过的西游故事编辑而成的,性质是 “ 编撰”,因此有一些西游故事本是勾栏瓦舍里几代说话艺人的创造,那一些讲故事的艺人大多是乡教授而已,不用说对佛经教义不懂,就是历史事实有一些也是似是而非的———例如将魏征称为“丞相”(《西游记》第九回)。
在诸多研究《西游记》成书的著作中,关于俗讲变文与说话艺术对西游故事以及这部小说生成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因此有探讨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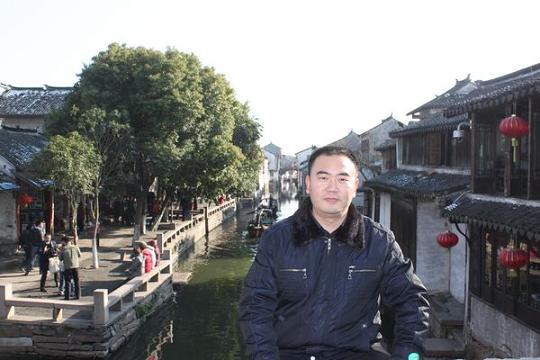
作者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俗讲
《汉语词典》对“俗讲”的解释:“院讲经形式。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佛学大词典》对“俗讲”的解释:“谓以在俗者为对象之讲经。开讲之僧,称俗讲僧。所说之资料皆属故事之类,为一种以平易通俗体裁解说佛教经典内容之法会,盛行于唐代、五代。”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善伏传》载:善伏于贞观三年(629)曾在常州义兴(江苏宜兴)听俗讲,其后皈依佛教。可知俗讲于贞观年间在常州地方即已开讲。有唐一代,俗讲普及于各地,在长安,有奉敕令而举行一个月者(一年三次,于正月、五月、九月等三长斋月各行一月),亦有于地方寺院举行短期之俗讲者。所开讲之经,较常见者,有《法华》《涅槃》《金刚》《华严》《般若》等大乘经典。又据敦煌文献载,知我国边疆地区俗讲亦十分普及。
俗讲变文的起源,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有主张直接仿自佛经体裁的(如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或谓起源于南朝转读唱导(如向达的《唐代俗讲考》),或起于古代之韵文者(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或起于清商旧乐的变歌(向达《唐代俗讲考》),或起于变相(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 [2]。
也有学者认为俗讲深受古印度说唱艺术的影响,如吕超在《印度表演艺术与敦煌变文讲唱》中认为,“以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代表的印度世俗讲唱艺术也极有可能传入敦煌地区。《罗摩衍那》虽然没有汉文译本,但其故事曾在新疆、吐蕃广泛流播。就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献来看,除了梵文本《罗摩衍那》外,尚有于阗文(中古伊朗语)、吐蕃文、吐火罗文、回鹘文等多种语言的译本或改编本。考虑到早期藏语七音节诗,甚至‘在韵律方面也受到印度格言诗作的影响’,我们便可以推断:传入西域、吐蕃的印度史诗弹唱表演,很可能依附于当地的曲艺活动而来到敦煌,进而影响变文讲唱。” [3]中国先秦固然存在着优伶演唱,如《周礼·春官》载有瞽人向民间妇女“诵诗,道正事”,但无论是规模、形式还是影响,都无法与古印度演唱艺术相比,我们看古印度两大史诗,其中的叙事经常提到说唱艺人跟随着战争的进展以及对于战事的讲唱 。[4]
俗讲,人们误以为始自中唐。其实,这是错误的。俗讲伴随着佛教的东传就已开始了,只不过中唐时大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已,之前就有很多关于俗讲的记载。例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颁布《禁僧徒敛财诏》,就明令禁止僧徒对俗众宣讲。它说:“近日僧徒……因缘讲说,眩惑州闾,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或出入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乡村,恣行教化。……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之外,一切禁断。”
安史之乱后,诸侯割据,百姓贫苦,这就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于是俗讲大兴。皇帝也明令规定长安中的寺庙在长斋月开讲。皇室、渔民等都去听讲。道教之徒也学习佛教俗讲的形式而开讲。民间艺人也开讲以糊口。
日本学者平野显昭认为,俗讲与“正讲”相对,是“讲于俗律”的意思,而不是“以庶民大众为对象的讲经” [5]。通常,人们都以为俗讲与“僧讲”相对,并将俗讲界定为面向世俗大众的说唱。其实,无论是俗讲还是僧讲,都是僧人的讲唱,都是僧人以讲故事的形式来演说 “ 佛法”,只不过俗众更喜欢听其中的故事,于是寺院便渐渐成为了戏场,以至于上至皇帝下至渔民都去听讲。后来,民间艺人受其影响和启发,也以“看图说话”的方式演说故事,从而谋一口饭食。再后来,随着技艺的精进,索性去掉了图画,发展成为了“口技”,如宋代瓦舍勾栏中的说话,到了元代又演变为平话。
佛教自创立伊始,就是以譬喻、故事等来演说其佛理。佛教的传播也是这种方式。佛教本是口头传法,后来才有了四大结集[6]。即使是书面的佛经,大多也是以故事阐释经义。譬如《贤愚经》,陈寅恪先生认为它 “ 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记,今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日中央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 [7]
有学人认为俗讲是受中国民间讲故事的影响才形成的,如李褰《唐话本初探》认为,“唐代说话是在古代的宫廷优人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路工《唐代的说话与变文》说:“变文的出现,比我国说唱文学出现的时间迟得多,应该说变文是吸取了我国说唱文学的营养发展起来的。” [8]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则认为“主要是市民和市民的‘说话’影响了俗讲”。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其实,是佛教的俗讲刺激和激发了中国说话艺术的蓬勃发展,是俗讲变文影响和刺激了中国固有的说话因素———作为讲故事的说话,当然讲故事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了,但是真正作为一种艺术和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是商业化的结果。而其艺术性却是受到了俗讲变文的影响之后历代说话艺人经过打磨而成的,从而使之发达起来了。
俗讲是佛教说“法”的形式之一。佛教东传到中土后,先是寺院里依然参照古印度的做法进行正说和俗讲。寺院中的俗讲由于有趣逗乐,因此俗众都乐意去听,并且在听讲的过程中慷慨地对寺院进行施舍。民间艺人受到启发,学习俗讲的演说方法,以演义历史故事、时事故事,甚至也演讲一些佛经故事。道教也模仿和学习俗讲的方法,但一般不及佛教的俗讲之精彩,所以有时候就用女冠开讲道经以吸引观众[9]。
玄奘回国后应唐太宗之请口述了《大唐西域记》,由其弟子辨机笔录成书。玄奘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琮又专门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人对《西游记》成书的源流考察最早追溯到这本书,但我认为俗讲中的西游故事才是小说《西游记》的本源。历史上的玄奘和尚去天竺游学的史实何以成为了神话传说中的西游故事?这是俗讲的功绩,由于俗讲除了要借助佛本生故事来说 “ 法”,还借助历史故事,甚至是时事故事来演说、宣传佛教之教义,而玄奘和尚取经的故事显然更适合俗讲弘法的需要,所以西游故事首先生成于俗讲之中,后经勾栏瓦舍里的说话即说诨经、说参请等添枝加叶,从而更加丰富了西游故事。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版者前言》也说: “书里面的这些诗,虽然都是中国七言(也有三言和五言)诗歌的形式,性质却接近佛经的偈赞;话文也和佛经相近;因此,它的体裁与唐朝、五代的‘讲唱经文’的‘俗讲’类似,可能受了它们的影响。”而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间蠡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中的语音是唐五代的西北方言,语法有别于宋人话本,语汇与变文同时,形制也是俗讲变文的规范。[10]蔡铁鹰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并不像一般文学史所采信的那样,是南宋临安出现的说经话本,而是晚唐时出现在西北敦煌一带的寺院俗讲底本 ” [11]。《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俗讲变文的结果,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恐怕未必仅仅只是 “西北敦煌一带”寺院里的俗讲变文。
胡胜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寺院俗讲’的性质决定了作品浓重的‘弘佛’倾向(这从其他情节也可感知,比如猴行者的自愿加盟,深沙神的化桥渡人,大梵天王神号的威力无边等。” [12]
蔡铁鹰在其《西北万里行,艰难欣喜两心知》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并没有详细回答,而是一笔带过。这个问题是:西域取经故事系统是如何传入内地的?[13]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通过俗讲传入内地的。俗讲随着佛教的东传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形成规模、兴盛起来的时间却是在中唐。正是俗讲,将已有传奇、神话色彩的玄奘取经故事敷演开来,它历经晚唐、五代、南北宋,至元代形成西游平话、西游杂剧等。到晚明的时候,市民文学兴盛,可能是由吴承恩集撰成书。
《西游记》说果报、说因缘与俗讲
从俗讲说“法”、劝惩崇佛这个角度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游记》的主旨,即《西游记》不是“阶级斗争”,不是“人才说”,而是自我的救赎。《西游记》其他的主旨理解都不能与文本的整体性相契合,如有的侧重于前七回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反抗精神;有的侧重于后半部分的斗法、取经、终成正果等,但只有从自我的救赎来解释,才能完整地把握小说整个文本的意义:唐僧即金蝉子,因为不认真听佛祖说 “法”,所以必须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完成自我救赎,成了正果;孙悟空因为大闹天宫,触犯天条,因此虽然他一个筋斗就能到西天,但也必须历经种种苦难以后才能成佛;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因为好色,在天宫里醉酒后调戏嫦娥,所以也被贬到下界,错投猪胎,需要遭受磨难,进行自我救赎;沙僧是天宫里的卷帘大将,因为工作失职,在宴会上打碎了琉璃盏所以也必须进行自我救赎。甚至白马即小白龙本是西海敖闰之子,因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父亲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不孝之死罪,是观音菩萨亲见玉帝,讨他下来,叫他与唐僧做个脚力,也是自我救赎;甚至某些神仙妖怪因为过失被罚到人世间进行自我救赎 …… 通过经历各种苦难以获得解脱,这是古印度一些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苦行意识的信念。古印度宗教很多,但大多赞同苦行。因此,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中不乏各种苦行的故事,其中就有被流放到森林里去苦行十几年,如《罗摩衍那》中的罗摩,自我流放到森林里十四年,完成自我救赎之后,又回去做国王等。
小说中的唐僧其前身是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为什么被罚到人世间进行自我救赎?就是因为他不认真听佛祖说“法”。显然,这是俗讲时讲师或法师吓唬听众的伎俩,即你们也要认真听讲,否则就会像金蝉子一样在来世受苦受罪的。《西游记》第一百回“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中,如来对唐僧说道:“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这就说明唐僧遭受磨难是有其因果的。
唐僧西天取经的缘起即《唐太宗入冥记》也是一个说因缘的故事,即魏徵“他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乃安邦立国之大宰辅也。因他梦斩了泾河龙王,那龙王告到阴司,说我王(唐太宗)许救又杀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渐觉身危。魏徵又写书一封,与我王带至冥司,寄与酆都城判官崔昚。少时,唐王身死,至三日复得回生。亏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书,加王二十年寿。今要做水陆大会,故遣贫僧远涉道途,询求诸国,拜佛祖,取大乘经三藏,超度孽苦升天也。”(第六十八回)
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是通过说因缘来结撰的,如朱紫国国王病了三年,与王后分别三载就是如此。孙悟空使计骗得金毛犼妖怪金铃,溜出洞外挑战,引出那妖怪,用铃摇出烟、沙、火,使那怪走投无路。观音洒甘露救火,并言此怪是自己坐骑,因报国王射伤孔雀大明王菩萨子女之恨,来此拆散国王鸾凤:
菩萨道: “ 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狲。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行者闻言急欠身道:“菩萨反说了,他在这里欺君骗后,败俗伤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 菩萨道:“你不知之,当时朱紫国先王在位之时,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间,极好射猎。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正来到落凤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开处,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佛母忏悔以后,吩咐教他拆凤三年,身耽啾疾。那时节,我跨着这犼,同听此言,不期这孽畜留心,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至今三年,冤愆满足,幸你来救治王患,我特来收妖邪也。”(第七十一回)
再如天竺国公主抛绣球打中唐僧,要与唐僧婚媾,被孙悟空看破她是假公主,当孙悟空正要一棒打杀她时,忽听得九霄碧汉之间,有人请他棍下留情!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太阴告诉悟空那个妖邪是她广寒宫捣玄霜仙药的玉兔。行者说那个玉兔摄藏了天竺国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他圣僧师父之元阳。其情其罪,其实何甘!怎么便可轻恕饶他?太阴便解释其中的因缘,说“:你亦不知。那国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宫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儿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灵之光,遂投胎于国王正宫皇后之腹,当时得以降生。这玉兔儿怀那一掌之仇,故于旧年走出广寒,抛素娥于荒野。但只是不该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逭。幸汝留心,识破真假,却也未曾伤损你师。万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这些因果,老孙也不敢抗违。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儿,恐那国王不信,敢烦太阴君同众仙妹将玉兔儿拿到那厢,对国王明证明证。一则显老孙之手段,二来说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后着那国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见显报之意也。”太阴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 “那孽畜还不归正同来!”玉兔儿打个滚,现了原身。(第九十五回)这显然也是说因缘了,唐僧西天取经所遭受的八十一难中有很多都是这些说因缘以结撰的。
不用再多列举了,《西游记》中的西游故事,大多都是因果报应的叙事。从小说文本中的西游故事可以推知,它们大多是俗讲或说因缘的产物。
《西游记》文本中的说唱因素与俗讲、说话
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认为:“唐代白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佛教和民众娱乐的关系很密切,唐代寺院往往也是民众娱乐的中心。两方面的因素必然推进白话文学的发展也会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头文学的发展。” [14]我们从关于“俗讲”的文献记载可知,上至皇帝、公主,下至市民百姓,都喜欢到寺院里去听俗讲。道教徒乃至于民间艺人也都效法说唱这一方式,于是“诗话”“、词话”等大兴。而今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然是南宋所刻,但玄奘取经故事不排除自中唐就已经在寺院里演说开来了。
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李诩在其《戒庵老人漫笔》 “ 禅玄二门唱”条下云:“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颂,词说如《西游记》《蓝关记》,实匹休耳。”(卷五)《蓝关记》讲述的是关于韩湘子的道教故事,属于道教之道情;《西游记》则属于佛家抛颂。可见当时确有僧人以讲唱的方式向民众传播《西游记》等故事。
李贽《西游记》评第一回侧评说:“凡西游诗赋,只要好听,原为只说而设。若以文理求之,则腐矣。” [15]李贽的这一个评点,实在是抓住了《西游记》说唱的本质。谢肇淛:“俗传有《西游记演义》,载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祟甚多,读者皆嗤其俚妄。” 而 “ 俚妄 ” 二字正说明了《西游记》的 “ 里谐于耳 ” 的世俗性、通俗性和说唱性。
刘荫柏认为《西游记》具有很鲜明的说唱特色。[16]他在《〈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中说“:小说残留着说唱文学的痕迹。孙悟空每次出场,都要谈一下出身历史光辉的战斗业绩,在戏曲中这叫自报家门。《西游记》中这样的情节大概有十几次,每次的内容都差不了多少。这就是说唱文学的特点。” [17]根据刘荫柏的考证,《西游记》中有很多“说唱痕迹”。这些“说唱痕迹”或即宋之说话中的说经或之前俗讲的影子。
纪德君认为,《西游记》中的民间说唱遗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通俗唱词的大量穿插;故事情节模式化现象比较突出;民间俗语的频繁使用。这些残存的民间说唱痕迹说明《西游记》确曾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或许其前身就是一种 “词话” [18]。而西游“词话”的前身或本身就是关于西游故事的俗讲。
柴剑虹则从“作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韵语或铺叙,或描述,状物写景,均与散文部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极少有重复累赘之感”、“体式多样,节奏感强,即便是杂言歌赋,也无论长短,仍然讲求句式整齐”和“语言生动活泼,尤多通俗风趣之语,和全书‘杂以诙谐,间以刺讽’(郑振铎语)的风格相统一” 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游记》中的韵语与敦煌讲唱文学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着“《西游记》这一类小说对唐五代讲唱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的渊源关系” [19]。
毋庸置疑,《西游记》文本中充斥着说书的口吻,具有讲唱结合的特点。中国隋唐之前固然有讲故事的事实,但是他们仅仅是讲故事,而俗讲显然是以讲唱相结合的艺术。这是由于俗讲本是佛教说“法”的方式之一,因而深受印度梵文学口头艺术形式的影响,即形式是韵散结合。散文用以讲说故事、铺陈情节,而韵文则往往是对相关故事的归纳或概括。“有诗为证”云云是大家最熟悉的。我们知道,印度的历史主要是口传的历史,为了便于记诵,都是采用韵文以概括以上讲过的故事的大意或是引起下文的。中国章回小说所采用的韵散结合,主要是受了它的影响(途径是经过汉译佛经),而不是像有的学人所说的是为了攀附诗歌的正统性。而我们也发现,中国章回小说中的韵文,除了专门描写风景的之外,也都是具有概括上文或引起下文的作用。而对风景的描述,其实也是古印度梵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通过汉译佛经而传入东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