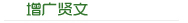孔子的世界性意义
2013年02月20日
二○一一年十一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出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孙立新教授做了题为《卫礼贤组建“尊孔学社”史实考》的报告,这同样引发了我对卫礼贤对孔子认识的兴趣。之后翻阅了孙教授同样提到的卫礼贤的夫人萨洛莫·威廉(萨美懿,SalomeWilhelm,1879-1958,娘家姓Blumhardt)所写的回忆录《卫礼贤——中欧间的精神纽带》(SalomeWilhelm〔Hrsg〕,RichardWilhelm.DergeistigeMittlerzwischenChinaundEuropa.Kln/Düsseldorf:EugenDiederichsVerlag,1965。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及其他相关的书籍,对卫礼贤对孔子思想的世界性意义的阐述进行了一些探究,发现其中的确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用心思考的。

在国外开办的孔子学院
一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尉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于一九一三年在青岛建立了“尊孔文社”,其阵容非常强大。据萨洛莫的回忆,当时在青岛德国租界中“避难”的前清贵族、官员、学者很多人都加入了文社:当时已经七十八岁的周馥,其子财政总长周学熙,大总统徐世昌及其兄弟徐世光,两江总督张人骏,最终任奉天都督的赵尔巽,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劳乃宣,以及翰林院编修商衍瀛等等(220—221页)。当时之青岛可谓汇集了晚清最重要的学者。卫礼贤在阐述“尊孔学社”的宗旨时指出:“我们那时的想法是为了未来拯救那些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的瑰宝。通过翻译、讲座以及学术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的精神领域建立联系,并进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汉语,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的青岛能够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青岛位于山海之间,悠闲宁静”(RichardWilhelm,DieSeeleChinas.Wiesbaden:marixverlag.2009.S.182-183)因此,“尊孔文社”并非单向地弘扬孔子的学说,而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
萨洛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卫礼贤与尊孔学社其他成员的共同声明,这是在回应由袁世凯掌控的《京报》(PekingGazette)“是否应当将孔教提升为国教”时的回答:
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看,它从来没有过国教。孔子也未想到过要建立一种新的教派。他无非是要传承与神的永恒意志相一致的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伟大法则。他没有要求成为宗教的创始人。他仅仅希望传授真理,并指明在世间达至秩序与和平之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理。不存在任何界限可能将真理限制在某些人组成的特别的集团之中,这些人仅属于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排斥其他教派。涉及到这一真理的学说,并不存在等级差别和种族差别。只要遵循这一学说,不论是谁,都会获得真理。拥有这一生命的智慧是孔子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对他来讲并不存在一个能建立起教派组织的空间,这一组织会将其自身与人类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孔子没有要求个人崇拜,这点毋庸赘述。他确实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想要获得真理跟他个人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求自己的弟子除了勤奋地遵循永恒的真理之外,别无他求。孔子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为所有的人开启了真理的大门,而没有任何教派的界限。儒家学派一直到今天都忠诚于这一榜样。尽管孔子为各代统治者所敬仰,但从来没有谁想到将儒家学说宣布为国教。就像很少有某处的某人想到将空气或水看做国家的空气或国家的水一样。空气和水之存在,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究竟它属于哪个国家或哪家教派,根本是无所谓的。真理的情形也不例外。世上本没有什么国家真理,就这点而言,如果说儒家所讲述的无非是真理的话,那它根本不能成为国教。每一类似的组织都会损害孔子的名誉,都会限制儒家真理必然的影响范围。没有一个真正的儒者会认为,对他的老师(孔子)而言,生活在一个儒教已经降格为一个宗派的社会中,是一种荣耀……东西方的伟大学说必然都不能作为单个国家的特别财产所拥有,这一时代已经到来。儒家学说有很多方面对于西方社会同样具有极大价值。因此,对孔子的尊崇最好的路径是使他的学说能在全世界广为人知。(224—225页)
卫礼贤对孔子学说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思考,上述的一段话既是对当时想要将孔教设立为国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回应,同时也阐明了孔子学说的全球意义和当代价值。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五日由陈焕章(一八八○——一九三三)等人创立于上海的“孔教会”的代表向当时的国会请愿,希望“守孔教为国教”,后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否决的第一条理由便是“激起宗教之纷争”(艾知命:《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收入《民国经世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六年版,第39册,60页)。卫礼贤同样对基督新教所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教派思想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此处所指的是他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国心灵》〔DieSeeleChinas〕,本文所引系上揭二○○九年重印本)。
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卫礼贤也指出:“不断侵入中国的欧洲西方文化也许是它(指孔子的学说——引者注)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对手。初看起来,古老的儒家学说似乎在被迫节节败退之后,到今天已最后终结了。但还不能作出最终结论,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具有适应现代环境的内在灵活性。可以肯定的是,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数年间所进行的、通过将儒学确立为国教而使基督教面对有效竞争的尝试必将失败,因为这种尝试只是从表面上移植了在本国已受到怀疑且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教会形式。”(卫礼贤《儒家学说的精髓》,收入蒋锐编译《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七年版,129页)
此外,卫礼贤从中国和欧洲当时的形势出发,坚定地认为,孔子的学说理应属于全世界,而不应当仅仅属于中国的某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自问道:什么是奠定中国和东方最深入、最根本的力量?东方给我们提供的决定性的认识是什么?东方的哪些光亮照亮了西方及其发展?我们进一步可以问道,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目前的状况下可以预见哪些结果和变化?西方能够为这些变化提供准则和解释吗?”(上揭《中国心灵》,363页)正是带着这些当代的问题意识,卫礼贤开始到孔子那里去寻求答案。
二
卫礼贤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以当时的问题意识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转化,这正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意义所在。早在一九○○年左右,世纪转折时期的欧洲感伤主义者们试图在文化危机之中抛弃日益趋于没落的西方文化,转而研究遥远东方的思想,即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思想。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从前常常被他们一贯鼓吹的西方文明开始腐烂变质。“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救世主选中的拯救对象,在骚动的欧洲知识界不时起着或永久或临时的振奋和拯救作用。”(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载《国际汉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二○○二年版,82页)《西方的没落》(UntergangdesAbendlandes,1918-1922)一书的作者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恰在此时以锋芒逼人的笔端道破了普遍不安的社会心态。他曾对传统历史的基本分期法(古代、中世纪、近代)以及西方对非欧洲文化的漠视提出异议,建议欧洲的知识分子应当把视线移到东方,以摆脱自身的困境(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5页)。他认为,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危机,更是没落。正因为此,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介绍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说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所谓“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重要思想,由“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仍然是几大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西方为例,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无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的力量:
至今人类依然靠着那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东西生活。每值新的飞跃产生之时,人们都会带着记忆重新回归到那轴心时代,并被它重燃激情。从此之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轴心时代力量的回忆以及复苏——复兴(Renaissancen)——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振奋。对这一开端的回归乃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件。(KarlJaspers,VomUrsprungundZielderGeschichte,München:R.Piper&Co.Verlag,1949,S.2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理论中,思想、伦理、宗教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对于判断历史进步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时期,而是找寻到了一个标准的参照坐标,以便于人们更公允地去关注历史,去从事异域陌生民族思想、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