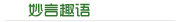在当地,邮递员还有一项必备的重要技能--过溜索。尼玛拉木的邮路横跨澜沧江,两根辫子粗细用铁丝拧成的溜索从60多米宽的江面上横过,溜索下就是滚滚的澜沧江。正是这两根溜索连通了澜沧江两岸的交通,成为河两岸村民往来的惟一通道。奔腾咆哮的江水曾吞噬过不少路人的生命,因此也被当地村民称为“吃人江”。几年前一位汉族志愿者在溜索处不幸坠江。一名邮递员和电信员也因赶时间合坐溜索,结果因为溜索绳子断开而坠江身亡。更让她心悸的是,她16岁的弟弟也是在澜沧江里出事的--捉鱼时不慎掉进江里,再也没上来过。这些都在尼玛拉木的心理留下了浓浓的阴影。但是当她想到这是送邮件的必经之路,索道那头还有乡亲们日日盼望着来自远方家人的信件时,她闭上眼睛坐上了溜索。如此几次下来,她也就慢慢习惯啦,这些年下来,尼玛拉木在这条溜索上来来回回1500多次啦。
尼玛拉木身高只有1.5米,体重也只有40多公斤,而她的邮包最轻时也有30斤,最重时五六十斤,“背不动也要背,因为是老乡们需要的,再苦再累也是必须的、值得的。”
她将这些信件视作生命,宁可自己受苦,也决不让信件破损。
雪域高原上的天气多变,这会儿还是晴空万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大雨瓢泼。尼玛拉木就吃过这样的苦头。有一次,尼玛拉木看着天气晴朗,就没有带雨具,结果行走在一个山崖间时突然下起了大雨。“邮件决不能受潮,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于是,她迅速找到一块大石头,把邮件藏在石头下,保护好。而她自己站在雨里,听任雨打风吹,又冷又饿又害怕,直到傍晚雨停才继续赶路。从那以后,尼玛拉木每次出行都带着3块不同大小的“油布”,小的包裹邮件,中等的包裹邮包,而大的自己使用。“这样既不会弄湿邮件,也不耽搁行程,还可以将信早点送出早点回家”,尼玛拉木说。
在绵延漫长的雪线邮路上,尼玛拉木遭遇的比风雪还恐怖的是内心的寂寞。德钦县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8个人,经常走几个小时都看不见一个人。只身翻山越岭,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极限的考验。尼玛拉木常常是边走边唱歌,用歌声来排挤孤单和焦虑。这样的环境对于一名男邮递员来说,都是艰巨的考验,更何况尼玛拉木这样一个仅90多斤的瘦弱女子呢?但是她能坚持,她说:“看到父老乡亲们打开报刊和信件时那种开心的模样,我的心里象灌进了一勺蜜,再辛苦也觉得是值得的!”
2001年5月,怀孕九月的尼玛拉木就要临产,她没有歇息,照样行走在邮路上。虽说藏族农村妇女们习惯怀孕也不肯闲着,可以继续做家务活,但是一想到尼玛拉木要挺着个大肚子,背着几十斤重的邮包,翻山越岭,溜索过江,老所长桑称还是心里不落忍,劝她休息。尼玛拉木说:“再跑两趟吧,我们农村妇女临产前还在地里劳动呢!”最后还是桑称强行“没收”了她的邮包,自己去跑邮路,她才肯歇下来。
但是,产后才20天,尼玛拉木就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照看,靠村里好心人喂奶和家里两头牦牛的奶喂养,她又重返邮路。
尼玛拉木的丈夫阿西布是尼玛拉木的同班同学。自从尼玛拉木当上邮递员后,他的生活就彻底颠覆了:他带孩子,做农活,做饭,干了尼玛拉木过去的活计。尼玛拉木要出班的时候,他还要起大早,帮她准备路上的干粮。由于忙着工作,照看孩子、做家务的活计,尼玛拉木都留给了丈夫,以至于丈夫被邻居们笑称为“尼玛拉木的媳妇”。
就这样,在家人的支持下,尼玛拉木认真工作,以艰苦的努力创下了无一封死信的纪录,从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投递准确率达到100%。
“邮包越重,老百姓越是开心,我就越开心”
现如今,尼玛拉木的邮包里不仅有远方亲人的信件,还有给乡亲们的报刊杂志,此外也有大山深处老乡们托她代购的部分小商品,比如药品、盐巴、针线、电话充值卡等类的东西。虽然这些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尼玛拉木一想到乡亲们迎接她的笑脸时,立刻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滋味。她说:“我背上的邮包越重,老百姓就越开心,我也就越自豪。”
尼玛拉木十几年如一日地行走在雪山峻岭上,每日背着沉甸甸的邮包,她深知自己肩上背的不仅仅是普通的邮件,更承载了藏族乡亲们对远方家人深深的思念。
今后的邮路依然艰辛而漫长,被社会和乡亲们广为认可尼玛拉木感到责任也越来越大。她说:“只要老百姓开心,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