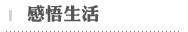唯有故乡不可修改
2013年11月12日

村道终于重修了,铺上了厚厚的水泥,路面比两边巷子的地面高出许多。因为这个坡度,从巷子里开着摩托车出来,到了巷口总要加速才能上得去。刚回老家时不知其中风险,开着摩托就往上冲,结果险些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撞翻。惊魂未定,司机从窗口伸出头来,朝我大吼,意思是闲杂人别到路上来添乱。新路平坦,车来车往,我扶着摩托车在路边发了一会儿呆,心里老觉得哪里不对劲。我似乎成了故乡路的陌路人。
公路属于司机,这个道理似乎是成立的。但在我的记忆中,这条路曾经属于鹅群、奔跑的少年和啄食稻谷的鸟儿。公路也并非被司机抢走,抢走公路的是时间。我站得很高,极目看去,路面平整如砌好的麻将牌,一直延伸到远方,正好将村子劈成左右两半,左边是一排排的住宅,右边是一块块的方田。
我一直将这条路当成是村子的一部分,就如饺子的折缝是饺子的一部分。当我还是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少年,这路曾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我将自行车骑得飞快,准确地绕过路上的小石头和小水洼,仿佛自得地骑着一匹飞马,成为小泥路的一部分。我16岁那年,路面终于被修平,铺上一层薄薄的水泥,泥水路升级成水泥路。夏天收稻时节,阳光如火,又平又滑的路面被晒成一个长条形的平底锅。水田里运来的稻谷颗颗饱满而湿润,被倾倒在这水泥路上,铺开来晒干。往来的车辆,都诚惶诚恐走在道路中间那窄窄的小道上,而路肩那两片金黄是碾压不得的。金黄的稻谷也曾是村道的一部分。
于是所有的车都开得很慢,所有的车都小心翼翼。车辆从远处来,只不过是融入了一片金黄之中,成为金黄的一部分;而不是切割,像现在这样,用速度将村子切断。
应该说,故乡的速度不是快或者慢,而是独立于城市的另一种频率。我曾经无限向往远方,希望仗剑走天涯,离开这个穷困自闭的地方。我跟发小虫虫说,一定得走,年轻人得出去闯荡。虫虫认为我是正确的,但自己并不为所动,没有想跟我一起出去的意思。他不读大学,中专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家乡;而我,像千万人那样离开家乡读大学找工作,然后留在陌生的城市。与上一代迁徙者不同——他们面对的基本是一个惰性气体一样稳定不变的家乡——而我们的家乡却是流动的。虫虫从小家庭条件就比我优越,我骑自行车,他骑摩托车;后来我买了摩托车,他已经买了汽车;几年前我也开着汽车回到故乡,暗想这下子应该赶上了吧,他不可能买飞机。结果回家一看,虫虫正在将一辆自行车装进他的汽车尾箱,他说以后他要骑自行车,这地方乡间小道环境好空气好,不骑自行车多可惜。这些年虫虫似乎越活越明白,而我却越活越迷茫。他做着小生意,心血来潮背着包就往西藏跑。他说,一起走。我摇头回答,走不开要上班。当然人生的活法没有谁比谁更好,探头探脑无非彼此羡慕,只要能活明白,知道自己要什么,人就会变得澄净。
只是每一个远行的人都有一个故乡梦。故乡不停地变化着,有一些质地又似乎纹丝不动。无数次在异乡的路口,我也疑惑自己当年的选择。一个人如何能够更有作为,或者能够更幸福,到底与遥远的追寻有没有关系?不知道。能够知道的是,对于远方的坚持不经意间让我成为故乡的叛逃者。一个转身我才发现,自己俨然成为故乡的异乡人。这里有许多人的生老病死再与我没有任何联系——逃离,这本是我多年前想要的,但现在我却发现有某些东西将我牢牢捆住,让我感觉自己在某个时刻也需要它。换言之,有故乡的人生活在一张人情网络之中,他们的大部分人生价值是在这张大网中被确定的;而我们,只是热情地奔忙,勇敢地接受陶铸,最后成为城市里一颗孤独的螺丝钉。这一颗螺丝钉和那一颗螺丝钉之间并没有网,却只有冰冷的铁块,它要求你坚硬、承载、有用。城市里没有真正的邻居,也没有真正的杯盏和茶壶,只有电梯里的彼此无视,相互戒备以保持彼此空间的相对完整。城市里让一切变得有用,那些无用的风景,荒草萋萋,枯树萧瑟,终究会被路面和楼层所替代。钢铁水泥的文明每前进一寸,泥土池塘便退后一尺,于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成为看不见的人情荒漠。
世界向前走,于是每个人不得不向前移动或四处迁徙。多年过去了,人情世故修改了我,推土机和公路修改了故乡,然而唯有心灵的故乡不可以被修改。有一股力量不允许它这么做,记忆固执地想保持原貌,甚至不惜美化它,给它以各种想象的装饰。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而这是幸还是不幸?或许每个人只能在梦里去重建一个故乡。只有梦里的故乡不会被修改,你可以重新回到狮头鹅的嘎嘎叫声里,回到金黄稻谷自然的香气之中,树木草石都会因为你的记忆而温润起来,骤雨敲击着瓦片,屋后会传来蛙鸣。只是一觉醒来,岁月的橡皮擦刚好也将一切梦境轻轻抹去了无痕迹。推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缓步而行,不禁想起谁说过的话: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你已不再是阳光少年。(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陈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