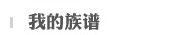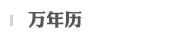几度沉浮的古花会
这种生机的重现,归功于民间、政府、学界的三重合力,也与中国的大环境大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饥荒、战乱都不出会,只有好年景、太平盛世了,才出会。”据王志计讲,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胜芳的花会一度中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恢复,“文革”开始之后又陷入停滞,火神庙等花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亦被拆毁。待1979年筹备恢复之时,胜芳的72道花会只剩下30多道。举办时间也顺应时代变革,从火神爷的生日改到了大家相对有闲暇的元宵节,从正月十二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胜芳花会在迎来了短暂兴盛之后,再度由于快速工业化浪潮的来袭而陷入低潮。直至2008年、2009年,古镇一期恢复工程以来,花会才又重现生机。今年的花会,仅参加表演的就有3000多人,这边厢,武术会的刀舞得银光四溅,那边厢,挎鼓会的锣鼓敲得震天响,观众或驻足围观,或拥簇着花会队伍向前行进,古镇不过3米多宽的巷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人家的(花会)都减少呢,说办不下去,俺们这儿不光没少,还恢复了几道会,还有新成立的今年就想要摆会,总会还得考虑考虑,不能破了老会的规矩不是。”谈到胜芳花会如今的发展,王志计满脸满眼的笑意。
“几方面原因吧。一是老百姓富裕了,闲时间也多了;二是国家把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得越来越高,电视上整天非遗非遗的,老头儿老太太都知道了;三是来的教授、学生多了,(他们)一说才知道,原来俺们身边有这么多宝贝,更得保护起来了。”胜芳古镇管委会主任张玉良,近年来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着胜芳传统民俗的保护,他把这种生机的重现,归功于民间、政府、学界的三重合力,同时他也提及,胜芳花会的兴衰一直以来就与中国的大环境、大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甘苦自知:花会背后的泪与笑
在拥有3000名演员、10万名观众的轰轰烈烈背后,胜芳花会也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75岁的王志计,从1979年至今一直是花会的三名主要会首之一,负责外联和协调事宜。“他老伴小脑萎缩,时刻不能离开人,但为了办会,他每天骑车骑上几公里赶到会里(会址在古镇最南端,他家在新区的北端);赶上摆会,还得跑政府、给小会送请帖。都70多岁的老人了,家里开着钢厂,放着清福不享,自己就骑着自行车完成这些。会首们都说,如果胜芳花会没有他这几十年来的跑上跑下,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王晟向我们转述了王志计的故事。
“还有各会的会首,都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正值创业的好时候。接一档会,就是一辈子的责任,胜芳的花会不光不交钱,还得每年给孩子们做新衣服,换新用具。你不活动会里没人,活动了自己家里的损失肯定不小,许多会每天晚上都得组织训练,又贴钱又贴时间,但他们几乎百分之百都坚持下来了。有几道会为了方便新镇区的孩子参加,还专门在那边成立了分会。”王晟说。
尽管胜芳大部分花会经济状况都不错,但也有少数在较差条件下坚持办会的。一位当地人说,前几天去一档武术会,正好看到会首和一位家长争吵,仔细一听,原来是为了谁掏钱为孩子们做衣服的事,家长看会里经济紧张,想自己出钱,会首却坚持,这是会里的老规矩,再困难也不能破。
如今,80后、90后也逐渐成为胜芳花会的主力阵容。镇里的两档高跷会,真正操心的就是两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许雯峰就是其中一位,每天晚上,他都准时去高跷会带徒弟,因为高跷训练容易受伤,必须在裸露的土地上训练,许雯峰牵头租了场地,还为会里添置了新的器材和服装,仅他个人去年为会里就花费一万多元。
王晟也是胜芳民间文化保护的重要人物之一,常年以“大孩子头”的网名活跃在网站和论坛上。他的真实身份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师,从2007年开始接触胜芳民俗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如今,他已是胜芳民间、政府与学界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人。“刚开始做田野调查人家花会不认可,一年冬至去跨鼓会,人家怕技艺外泄,不让进去,在门口从上午10点站到下午4点,也没采访成。还有一次为了采访,大雪天摔了一跤,腿紫了半个月。”不过这些都没阻止王晟继续进行他热爱的非遗调查,他还利用各种网站,宣传胜芳的历史文化。王晟的投入也曾一度被家人看作不务正业,但逐渐家人也开始转变态度,父亲今年还替他联系了一道消失近60年的昆曲班社。“他们也知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王晟说。
“没别的,就是喜欢,就是爱我们胜芳的一草一木,还有每一样传统,在胜芳人看来,这些都是宝贝,保护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责任。”采访的最后,当问及是何种力量支撑着他们走下去的时候,王晟赧然地笑了,他说自己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胜芳文化的信徒、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播者。(来源: 中国文化报)